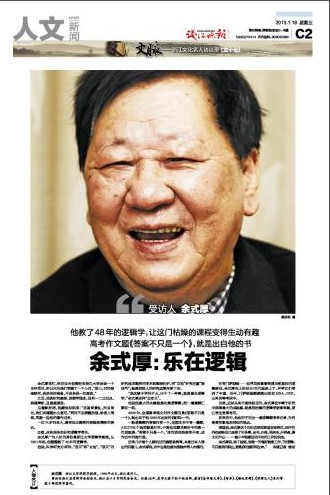
余式厚很忙,采访当天他要赶去浙江大学洽谈一个合作项目,所以只为我们预留了一个小时,“放心,时间保准够用,我早做好准备,不会多说一句废话。”
之后,他谈研究感受,谈教学理念,自列一二三四点,条理清晰,且层层递进。
见摄影拍照,他蹭地站起来:“这里背景乱,而且背光,我们去隔壁办公室吧。”同时不忘提醒助理,给客人倒茶,再搬一些他的著作过来。
一位74岁的老人,竟有如此缜密的思维和清晰的表达。
当然,这和他毕生研究逻辑学有关。
余式厚广为人知的身份是浙江大学逻辑学教授,从1961年起,他整整教了48年的逻辑学。
他说,科学研究分两种,“顶天”和“立地”。“顶天”的研究追求高深的学术和高端科研,而“立地”研究注重“接地气”,就是把前人的研究成果传承下去。
“我这辈子学问不大,只干了一件事,就是普及逻辑学。”余式厚这样“自定义”。
他说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收集逻辑题,把一道道题汇聚在一起。
2000年,全国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是《答案不只是一个》,就出自于他1999年出版的《智库》一书。
一般逻辑题的答案只有一个,但那本书中有一道题,ABCDE5个选项都是对的,于是他在题目解析中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答案不只是一个。”这句话很快流传开来,成为当年的流行语。
还有几乎每个人都玩过的脑筋急转弯,本是日本人想出的玩意儿,余式厚说,当年也是他首先接触并带入中国的。
还有门萨测验——世界顶级高智商俱乐部里玩的逻辑游戏,余式厚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迷上了,并将它们带进了中国。而今,门萨测验题频频出现在MBA、GRE、公务员等考试中。
当然,应试从来不是终极目的,余式厚在半辈子研究中获得最大的成就感,就是把枯燥的逻辑学变得有趣,更让学生觉得有用。
在采访中,他会时不时出一道逻辑题考考记者,为的是更形象地说明他的观点。
照理说,余式厚这个年纪应该在家里安享晚年,闲不住的他却给自己安排了许多事,出书、办报、做杂志、开讲座、搞文化产业……一副小年轻都自叹不如的工作狂状态。
余式厚说,除了抽烟,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工作,“而逻辑,不仅是我的职业,更是我的爱好和生命。”
人物名片
余式厚 浙江大学逻辑学教授。1938年出生,浙江温州人。
曾担任浙江省逻辑学会副会长、浙江省口才学研究会会长。任教48年,是学生眼中的个性老师,著有《金字塔文库》、《智库》、《趣味逻辑》、《逻辑达人》系列等数十部逻辑学著作。

几年前,余式厚偶遇一位学生,学生考他:“您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吗?”余式厚顺利接招,准确无误。
那时,距那位学生毕业已经四年了。学生回去后,给他寄来两斤开化龙顶,并附信一封述说感动。
茶叶是余式厚留给学生的特殊记忆。
他上逻辑课,没有厚厚的讲义,却一定带着茶叶、纸杯和热水瓶。学生随时可以讨杯茶喝,“逻辑学很枯燥,我要先让气氛愉快起来。”
他的课几乎百无禁忌,可以唱歌,也可以当场辩论。
学生上他的课,充满欢笑,也带着紧张,因为没准什么时候就会被他抛出的题目难住。
在学生眼里,他就是这么一位个性老师,有着孩童般的心态。
比如有时候一大早醒来,他会打一条短信——“似乎,生命才从今天开始”——他时常会冒出这些带点哲思的句子,然后群发给同学们共勉。
“我发短信可快了,有时候一天会发150条短信和学生交流。”余式厚得意地说。
(以下记者简称“记”,余式厚简称“余”)
【普及逻辑】 有道难题叫“谁养斑马”
我大量搜集习题,以前没电脑的时候,我都把题抄在卡片上,大约有3400多张,全是我从国外的著作上翻译过来的。
记:逻辑学素来以枯燥闻名,您是怎么迷上逻辑学的?
余:其实我大学里主修的是历史,选修逻辑学是觉得有趣,我很喜欢做逻辑题,没想到毕业后就留校教逻辑学了。
记:逻辑学是西方传入的,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如何?
余:逻辑学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,一个是数学逻辑,一个是语言逻辑,这两个研究方向都是“顶天”的。
比如我们的日常对话很生动,但计算机语言很死板,语言逻辑研究得好,就能让计算机听懂人类的自然语言。
这个研究也是国际上正在解决的大难题。
我的研究重心是逻辑普及,科研也需要接地气,接地气的意义是把前任的研究成果传承下去——西方的逻辑学作为外来学科,怎么让中国12亿人普及起来,知道这个知识,并且灵活地应用到生活中去。
记:那您做了哪些工作呢?
余:逻辑理论比较枯燥,所以我大量搜集有趣的逻辑题,让学生们能够快速领悟,并且对逻辑学产生兴趣。
以前没电脑的时候,我都把题抄在卡片上,大约有3400多张,全是我从国外的著作上翻译过来的。
比如我把门萨测验带进中国时,当时国内根本没有人研究,我自己花钱请外语学院的学生帮我翻译题目,然后我自己解题。
记:您解过的最难的一道题是什么?
余:最难的一道推理题叫“谁养斑马”。
题目是说有五个不同国籍的人,居住着五幢不同颜色的房子,他们各有不同的心爱动物(如斑马、狗等),喝不同的饮料(如水、茶等),抽不同的香烟。
然后给你14个已知条件,让你推理出谁是喝水的人?谁是养斑马的人?
据说上世纪60年代,美国大学生为了解这道题,几天几夜不睡觉。我做了一天半,独立解出来的。
记:现在的很多考试比如GRE、MBA、公务员等都要考逻辑,但做题对日常的逻辑应用真有帮助吗?
余:答题只是对逻辑应用能力的检验。所以这些逻辑测试中,不考逻辑知识,不考逻辑理论,只考你的逻辑应用能力。
记: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您的《逻辑达人》系列,11本书共300万字,包括逻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、各类考试中的逻辑题等等,怎么一口气出了那么多书?
余:都是我几十年的积累呀,我有一肚子的趣味逻辑题。
【开心老师】 让学生觉得有趣
我的逻辑课上,不讲逻辑史,简单梳理逻辑理论,重点培养逻辑应用,教大家如何推理,如何辩论。我的课学生都很爱听,每堂课必有笑声。
记:逻辑课通常都被认为很无聊,学生们会不会应付了事?
余:从某种意义上来看,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学科,因为它所处理的是纯粹抽象的东西。
但是,逻辑学又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学科,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,即我们自己的思维。
学校开这门课,就是让同学们能够将逻辑学运用到生活和学习中。我教逻辑学的目标,就是让学生觉得有趣,而且有用。
记:您是怎样让逻辑课变得有趣的?
余:我的四大教学法则是愉快教学、应用教学、交流教学和宽松教学。
我的逻辑课上,不讲逻辑史,简单梳理逻辑理论,重点培养逻辑应用,教大家如何推理,如何辩论。我的课学生都很爱听,每堂课必有笑声。
很多课都是开卷考试的,但我不干,也不会故意把题目出得很简单。48年里我教了5万多学生,不及格的只有一个,补考者不过百人。
记:您觉得当代大学生的逻辑能力如何?
余:条理不清楚,推理能力差,概念不明确,表达没有说服力,这些都是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缺陷。
上完我的课,至少他们会知道自己的缺陷在哪里。
记:您喜欢看《福尔摩斯》吗?这么问,是因为有的学生会把逻辑学当成侦探推理课来上。
余:非常喜欢,也很认同夏洛克的推理方法,但他的演绎法在故事中有些神化了。
我不能根据你的着装来推理出你今天早上听了什么音乐,这太理想化,不确定的因素太多。
但我会让女同学们知道,单单根据丈夫衬衫上的口红印就推理他有外遇,是会造成很大误会的。
其实说穿了,演绎推理没有什么神秘可言,就是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,任何人只要下点工夫都可以掌握。
【潮流学者】 私人购电脑,浙江他最早
你不觉得全是小年轻的课堂上,走进一个老头来教时尚,这种反差本身就已经很时尚了?
记:我的一些同事就是您的学生,听他们说,您是个特别时尚的人?
余:哈哈!我是浙江省私人购买电脑第一人,那是1987年,我花一万块买了一台比286还差的8088。
记:是为了赶潮流吗?
余:为了备课、写书更方便,我还喜欢研究排版软件,所以我出的很多书,都是我自己排版的。
我还会请人帮我画插画,让逻辑题变得更有趣。
记:听说您曾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开过一门叫“时尚与潮流”的选修课,这似乎和逻辑学没关系?
余:就是好胜心使然,年轻人能上的课我老余为什么不能上?
记:有个问题您别生气,一个老人在一群小年轻面前教时尚,会有说服力?
余:你不觉得全是小年轻的课堂上,走进一个老头来教时尚,这种反差本身就已经很时尚了?
我不会去讲那种很虚幻的时尚,而是从米兰、巴黎等城市的时尚现状说起,分析谁在操控现在的时尚,并介绍一些时尚观念、时尚文化和时尚产品。
记:那您最近在做什么时髦的事儿?
余:我正在研究一个课题——微逻辑。
现在不是很多事都被冠以“微”的名号,微博、微信、微小说、微电影,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了“微时代”。
当下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很快,为了顺应这种“微生活”,我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出5本书,用最精炼的语言,最经典的例子,教大家学逻辑。